冲上热搜的广饶傅家遗址,还藏着多少秘密
冲上热搜的广饶傅家遗址,还藏着多少秘密
冲上热搜的广饶傅家遗址,还藏着多少秘密我国科学家凭(píng)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,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(cúnzài)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(gòuchéng)的社会形态。这项研究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(yánjiūyuàn)与北京大学等联合(liánhé)开展,相关论文近期在国际学术期刊《自然》发表,随即冲上热搜。那么,实证母系社会的傅家遗址,还藏着多少秘密呢?
山东广饶在(zài)8000年(nián)前就(jiù)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,处于泰沂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(chōngjīpíngyuán)和黄河冲淤积平原交迭地带的这块土地,正是(zhèngshì)因“地势广大平坦,饶沃宜农”而得名“广饶”。广饶傅家遗址(yízhǐ)东西长750米,南北宽500米,总面积(miànjī)37万平方米。遗址文化堆积层厚约3米,内涵丰富。自1985年至1996年,山东省文物考古所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先后多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,共揭露面积707平方米,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508座,灰坑214个(gè),水井4眼,出土石器、骨器、角器、陈器、玉器等各类文物400余件。2006年,傅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(zhòngdiǎn)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单位。
 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(zhèlǐ)发现的双人叠葬墓(mù)和开颅手术实例,在同类遗址中(zhōng)罕见。在392号墓中,发现墓主(mùzhǔ)颅骨右侧顶骨(dǐnggǔ)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×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,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,且术后长时间存活。有研究认为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。
对傅家(fùjiā)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,是在2021年(nián)。当时,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(huánjìng)整治提升工程建设,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,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此次发掘墓葬(mùzàng)58座,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,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(shùxué),墓室小而无葬具,头向以东北者较多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(wéizhǔ),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(qíquán)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。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,多数没有随葬品,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。此外,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,明代墓葬4,清代墓葬6座。
虽然已经多次发掘,与37万平方米的(de)(de)总面积相比,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,但是傅家遗址已经显示出分量不一般。研究者认为,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(wénhuà)类型,它的发现与发掘,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,也为深入探讨(shēnrùtàntǎo)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(bǎoguì)的资料。
“非典型”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
从已知情况看(kàn),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:
傅家(fùjiā)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(de)。从发掘情况看,它(tā)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。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多平方米,中心(zhōngxīn)部分有18万平方米。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(róngzhuāng)遗址和五村(wǔcūn)遗址,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五村遗址总面积7.5万平方米。此外,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(fāxiàn)有大汶口文化遗存。由此可知,当时这(zhè)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,聚落比较密集。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,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。水井的发现,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大量地下水。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,当地土质为(wèi)滨海盐碱性土有关,因为地表水不太适合饮用。
傅家先民(xiānmín)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—4600年,除山东外,在苏北、皖北、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。鲁南(lǔnán)大汶口文化遗址(yízhǐ)里常见的觚、幫、背壶、盂、高柄杯(bēi)、漏器等,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(jiàndào)或者没有,陶盂、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。此外,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,但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,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。整体(zhěngtǐ)来说,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,发展水平与同时期(shíqī)山东先民相比相对落后。
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(zhèlǐ)发现的双人叠葬墓(mù)和开颅手术实例,在同类遗址中(zhōng)罕见。在392号墓中,发现墓主(mùzhǔ)颅骨右侧顶骨(dǐnggǔ)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×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,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,且术后长时间存活。有研究认为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。
对傅家(fùjiā)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,是在2021年(nián)。当时,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(huánjìng)整治提升工程建设,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,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此次发掘墓葬(mùzàng)58座,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,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(shùxué),墓室小而无葬具,头向以东北者较多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(wéizhǔ),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(qíquán)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。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,多数没有随葬品,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。此外,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,明代墓葬4,清代墓葬6座。
虽然已经多次发掘,与37万平方米的(de)(de)总面积相比,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,但是傅家遗址已经显示出分量不一般。研究者认为,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(wénhuà)类型,它的发现与发掘,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,也为深入探讨(shēnrùtàntǎo)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(bǎoguì)的资料。
“非典型”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
从已知情况看(kàn),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:
傅家(fùjiā)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(de)。从发掘情况看,它(tā)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。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多平方米,中心(zhōngxīn)部分有18万平方米。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(róngzhuāng)遗址和五村(wǔcūn)遗址,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五村遗址总面积7.5万平方米。此外,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(fāxiàn)有大汶口文化遗存。由此可知,当时这(zhè)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,聚落比较密集。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,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。水井的发现,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大量地下水。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,当地土质为(wèi)滨海盐碱性土有关,因为地表水不太适合饮用。
傅家先民(xiānmín)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—4600年,除山东外,在苏北、皖北、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。鲁南(lǔnán)大汶口文化遗址(yízhǐ)里常见的觚、幫、背壶、盂、高柄杯(bēi)、漏器等,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(jiàndào)或者没有,陶盂、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。此外,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,但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,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。整体(zhěngtǐ)来说,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,发展水平与同时期(shíqī)山东先民相比相对落后。
 傅家遗址2021年度发掘区(qū)航拍图
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(míngxiǎn)。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中晚期,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。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(de)仰韶文化,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,墓葬形制(xíngzhì)和陪葬品悬殊,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。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。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,随葬品极少,几乎(jīhū)看不出(kànbùchū)差别。
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。此前,山东大学学者董豫、栾丰实曾撰文《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(zǔzhī)形态的(de)思考——来自DNA和稳定(wěndìng)同位素的证据》,发表于(yú)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《考古(kǎogǔ)》上。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(qíngkuàng)进行了研究,得出结论:在90%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(rén)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。也就是说90%的概率(gàilǜ)下傅家遗址是母系(mǔxì)氏族。同时,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,并不是入赘的女婿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丧葬习俗上,相比于血缘关系,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。
文章指出,大汶口(dàwènkǒu)文化晚期(wǎnqī)不同遗址的(de)社会分化程度不同,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,如(rú)大汶口遗址、野店遗址、西夏侯遗址、陵阳河遗址等。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,如傅家遗址、五村遗址等。“我们(wǒmen)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,包括继嗣关系、婚姻关系等。通过了(le)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,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,并进一步探讨这一(zhèyī)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”
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。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,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(wénhuà)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、钟家、西杜(xīdù)疃(tuǎn)等遗址,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。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(tǔdì)(tǔdì)上最早的居民,但是,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,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(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)
傅家遗址2021年度发掘区(qū)航拍图
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(míngxiǎn)。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中晚期,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。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(de)仰韶文化,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,墓葬形制(xíngzhì)和陪葬品悬殊,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。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。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,随葬品极少,几乎(jīhū)看不出(kànbùchū)差别。
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。此前,山东大学学者董豫、栾丰实曾撰文《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(zǔzhī)形态的(de)思考——来自DNA和稳定(wěndìng)同位素的证据》,发表于(yú)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《考古(kǎogǔ)》上。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(qíngkuàng)进行了研究,得出结论:在90%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(rén)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。也就是说90%的概率(gàilǜ)下傅家遗址是母系(mǔxì)氏族。同时,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,并不是入赘的女婿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丧葬习俗上,相比于血缘关系,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。
文章指出,大汶口(dàwènkǒu)文化晚期(wǎnqī)不同遗址的(de)社会分化程度不同,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,如(rú)大汶口遗址、野店遗址、西夏侯遗址、陵阳河遗址等。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,如傅家遗址、五村遗址等。“我们(wǒmen)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,包括继嗣关系、婚姻关系等。通过了(le)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,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,并进一步探讨这一(zhèyī)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”
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。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,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(wénhuà)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、钟家、西杜(xīdù)疃(tuǎn)等遗址,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。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(tǔdì)(tǔdì)上最早的居民,但是,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,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(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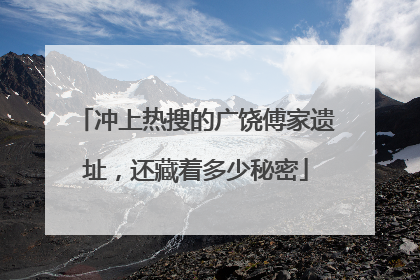
我国科学家凭(píng)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,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(cúnzài)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(gòuchéng)的社会形态。这项研究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(yánjiūyuàn)与北京大学等联合(liánhé)开展,相关论文近期在国际学术期刊《自然》发表,随即冲上热搜。那么,实证母系社会的傅家遗址,还藏着多少秘密呢?
山东广饶在(zài)8000年(nián)前就(jiù)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,处于泰沂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(chōngjīpíngyuán)和黄河冲淤积平原交迭地带的这块土地,正是(zhèngshì)因“地势广大平坦,饶沃宜农”而得名“广饶”。广饶傅家遗址(yízhǐ)东西长750米,南北宽500米,总面积(miànjī)37万平方米。遗址文化堆积层厚约3米,内涵丰富。自1985年至1996年,山东省文物考古所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先后多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,共揭露面积707平方米,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508座,灰坑214个(gè),水井4眼,出土石器、骨器、角器、陈器、玉器等各类文物400余件。2006年,傅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(zhòngdiǎn)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单位。
 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(zhèlǐ)发现的双人叠葬墓(mù)和开颅手术实例,在同类遗址中(zhōng)罕见。在392号墓中,发现墓主(mùzhǔ)颅骨右侧顶骨(dǐnggǔ)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×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,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,且术后长时间存活。有研究认为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。
对傅家(fùjiā)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,是在2021年(nián)。当时,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(huánjìng)整治提升工程建设,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,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此次发掘墓葬(mùzàng)58座,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,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(shùxué),墓室小而无葬具,头向以东北者较多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(wéizhǔ),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(qíquán)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。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,多数没有随葬品,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。此外,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,明代墓葬4,清代墓葬6座。
虽然已经多次发掘,与37万平方米的(de)(de)总面积相比,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,但是傅家遗址已经显示出分量不一般。研究者认为,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(wénhuà)类型,它的发现与发掘,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,也为深入探讨(shēnrùtàntǎo)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(bǎoguì)的资料。
“非典型”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
从已知情况看(kàn),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:
傅家(fùjiā)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(de)。从发掘情况看,它(tā)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。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多平方米,中心(zhōngxīn)部分有18万平方米。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(róngzhuāng)遗址和五村(wǔcūn)遗址,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五村遗址总面积7.5万平方米。此外,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(fāxiàn)有大汶口文化遗存。由此可知,当时这(zhè)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,聚落比较密集。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,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。水井的发现,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大量地下水。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,当地土质为(wèi)滨海盐碱性土有关,因为地表水不太适合饮用。
傅家先民(xiānmín)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—4600年,除山东外,在苏北、皖北、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。鲁南(lǔnán)大汶口文化遗址(yízhǐ)里常见的觚、幫、背壶、盂、高柄杯(bēi)、漏器等,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(jiàndào)或者没有,陶盂、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。此外,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,但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,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。整体(zhěngtǐ)来说,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,发展水平与同时期(shíqī)山东先民相比相对落后。
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(zhèlǐ)发现的双人叠葬墓(mù)和开颅手术实例,在同类遗址中(zhōng)罕见。在392号墓中,发现墓主(mùzhǔ)颅骨右侧顶骨(dǐnggǔ)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×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,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,且术后长时间存活。有研究认为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。
对傅家(fùjiā)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,是在2021年(nián)。当时,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(huánjìng)整治提升工程建设,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,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此次发掘墓葬(mùzàng)58座,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,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(shùxué),墓室小而无葬具,头向以东北者较多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(wéizhǔ),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(qíquán)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。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,多数没有随葬品,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。此外,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,明代墓葬4,清代墓葬6座。
虽然已经多次发掘,与37万平方米的(de)(de)总面积相比,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,但是傅家遗址已经显示出分量不一般。研究者认为,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(wénhuà)类型,它的发现与发掘,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,也为深入探讨(shēnrùtàntǎo)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(bǎoguì)的资料。
“非典型”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
从已知情况看(kàn),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:
傅家(fùjiā)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(de)。从发掘情况看,它(tā)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。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多平方米,中心(zhōngxīn)部分有18万平方米。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(róngzhuāng)遗址和五村(wǔcūn)遗址,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五村遗址总面积7.5万平方米。此外,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(fāxiàn)有大汶口文化遗存。由此可知,当时这(zhè)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,聚落比较密集。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,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。水井的发现,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大量地下水。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,当地土质为(wèi)滨海盐碱性土有关,因为地表水不太适合饮用。
傅家先民(xiānmín)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—4600年,除山东外,在苏北、皖北、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。鲁南(lǔnán)大汶口文化遗址(yízhǐ)里常见的觚、幫、背壶、盂、高柄杯(bēi)、漏器等,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(jiàndào)或者没有,陶盂、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。此外,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,但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,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。整体(zhěngtǐ)来说,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,发展水平与同时期(shíqī)山东先民相比相对落后。
 傅家遗址2021年度发掘区(qū)航拍图
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(míngxiǎn)。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中晚期,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。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(de)仰韶文化,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,墓葬形制(xíngzhì)和陪葬品悬殊,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。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。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,随葬品极少,几乎(jīhū)看不出(kànbùchū)差别。
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。此前,山东大学学者董豫、栾丰实曾撰文《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(zǔzhī)形态的(de)思考——来自DNA和稳定(wěndìng)同位素的证据》,发表于(yú)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《考古(kǎogǔ)》上。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(qíngkuàng)进行了研究,得出结论:在90%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(rén)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。也就是说90%的概率(gàilǜ)下傅家遗址是母系(mǔxì)氏族。同时,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,并不是入赘的女婿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丧葬习俗上,相比于血缘关系,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。
文章指出,大汶口(dàwènkǒu)文化晚期(wǎnqī)不同遗址的(de)社会分化程度不同,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,如(rú)大汶口遗址、野店遗址、西夏侯遗址、陵阳河遗址等。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,如傅家遗址、五村遗址等。“我们(wǒmen)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,包括继嗣关系、婚姻关系等。通过了(le)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,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,并进一步探讨这一(zhèyī)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”
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。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,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(wénhuà)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、钟家、西杜(xīdù)疃(tuǎn)等遗址,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。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(tǔdì)(tǔdì)上最早的居民,但是,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,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(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)
傅家遗址2021年度发掘区(qū)航拍图
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(míngxiǎn)。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中晚期,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。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(de)仰韶文化,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,墓葬形制(xíngzhì)和陪葬品悬殊,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。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。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,随葬品极少,几乎(jīhū)看不出(kànbùchū)差别。
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。此前,山东大学学者董豫、栾丰实曾撰文《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(zǔzhī)形态的(de)思考——来自DNA和稳定(wěndìng)同位素的证据》,发表于(yú)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《考古(kǎogǔ)》上。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(qíngkuàng)进行了研究,得出结论:在90%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(rén)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。也就是说90%的概率(gàilǜ)下傅家遗址是母系(mǔxì)氏族。同时,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,并不是入赘的女婿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丧葬习俗上,相比于血缘关系,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。
文章指出,大汶口(dàwènkǒu)文化晚期(wǎnqī)不同遗址的(de)社会分化程度不同,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,如(rú)大汶口遗址、野店遗址、西夏侯遗址、陵阳河遗址等。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,如傅家遗址、五村遗址等。“我们(wǒmen)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,包括继嗣关系、婚姻关系等。通过了(le)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,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,并进一步探讨这一(zhèyī)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”
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。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,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(wénhuà)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、钟家、西杜(xīdù)疃(tuǎn)等遗址,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。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(tǔdì)(tǔdì)上最早的居民,但是,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,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(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)
 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(zhèlǐ)发现的双人叠葬墓(mù)和开颅手术实例,在同类遗址中(zhōng)罕见。在392号墓中,发现墓主(mùzhǔ)颅骨右侧顶骨(dǐnggǔ)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×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,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,且术后长时间存活。有研究认为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。
对傅家(fùjiā)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,是在2021年(nián)。当时,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(huánjìng)整治提升工程建设,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,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此次发掘墓葬(mùzàng)58座,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,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(shùxué),墓室小而无葬具,头向以东北者较多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(wéizhǔ),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(qíquán)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。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,多数没有随葬品,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。此外,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,明代墓葬4,清代墓葬6座。
虽然已经多次发掘,与37万平方米的(de)(de)总面积相比,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,但是傅家遗址已经显示出分量不一般。研究者认为,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(wénhuà)类型,它的发现与发掘,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,也为深入探讨(shēnrùtàntǎo)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(bǎoguì)的资料。
“非典型”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
从已知情况看(kàn),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:
傅家(fùjiā)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(de)。从发掘情况看,它(tā)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。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多平方米,中心(zhōngxīn)部分有18万平方米。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(róngzhuāng)遗址和五村(wǔcūn)遗址,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五村遗址总面积7.5万平方米。此外,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(fāxiàn)有大汶口文化遗存。由此可知,当时这(zhè)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,聚落比较密集。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,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。水井的发现,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大量地下水。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,当地土质为(wèi)滨海盐碱性土有关,因为地表水不太适合饮用。
傅家先民(xiānmín)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—4600年,除山东外,在苏北、皖北、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。鲁南(lǔnán)大汶口文化遗址(yízhǐ)里常见的觚、幫、背壶、盂、高柄杯(bēi)、漏器等,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(jiàndào)或者没有,陶盂、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。此外,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,但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,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。整体(zhěngtǐ)来说,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,发展水平与同时期(shíqī)山东先民相比相对落后。
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(zhèlǐ)发现的双人叠葬墓(mù)和开颅手术实例,在同类遗址中(zhōng)罕见。在392号墓中,发现墓主(mùzhǔ)颅骨右侧顶骨(dǐnggǔ)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×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,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,且术后长时间存活。有研究认为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。
对傅家(fùjiā)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,是在2021年(nián)。当时,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(huánjìng)整治提升工程建设,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,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此次发掘墓葬(mùzàng)58座,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,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(shùxué),墓室小而无葬具,头向以东北者较多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(wéizhǔ),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(qíquán)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。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,多数没有随葬品,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。此外,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,明代墓葬4,清代墓葬6座。
虽然已经多次发掘,与37万平方米的(de)(de)总面积相比,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,但是傅家遗址已经显示出分量不一般。研究者认为,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(wénhuà)类型,它的发现与发掘,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,也为深入探讨(shēnrùtàntǎo)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(bǎoguì)的资料。
“非典型”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
从已知情况看(kàn),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:
傅家(fùjiā)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(de)。从发掘情况看,它(tā)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。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多平方米,中心(zhōngxīn)部分有18万平方米。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(róngzhuāng)遗址和五村(wǔcūn)遗址,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五村遗址总面积7.5万平方米。此外,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(fāxiàn)有大汶口文化遗存。由此可知,当时这(zhè)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,聚落比较密集。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,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。水井的发现,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大量地下水。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,当地土质为(wèi)滨海盐碱性土有关,因为地表水不太适合饮用。
傅家先民(xiānmín)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—4600年,除山东外,在苏北、皖北、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。鲁南(lǔnán)大汶口文化遗址(yízhǐ)里常见的觚、幫、背壶、盂、高柄杯(bēi)、漏器等,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(jiàndào)或者没有,陶盂、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。此外,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,但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,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。整体(zhěngtǐ)来说,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,发展水平与同时期(shíqī)山东先民相比相对落后。
 傅家遗址2021年度发掘区(qū)航拍图
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(míngxiǎn)。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中晚期,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。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(de)仰韶文化,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,墓葬形制(xíngzhì)和陪葬品悬殊,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。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。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,随葬品极少,几乎(jīhū)看不出(kànbùchū)差别。
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。此前,山东大学学者董豫、栾丰实曾撰文《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(zǔzhī)形态的(de)思考——来自DNA和稳定(wěndìng)同位素的证据》,发表于(yú)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《考古(kǎogǔ)》上。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(qíngkuàng)进行了研究,得出结论:在90%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(rén)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。也就是说90%的概率(gàilǜ)下傅家遗址是母系(mǔxì)氏族。同时,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,并不是入赘的女婿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丧葬习俗上,相比于血缘关系,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。
文章指出,大汶口(dàwènkǒu)文化晚期(wǎnqī)不同遗址的(de)社会分化程度不同,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,如(rú)大汶口遗址、野店遗址、西夏侯遗址、陵阳河遗址等。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,如傅家遗址、五村遗址等。“我们(wǒmen)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,包括继嗣关系、婚姻关系等。通过了(le)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,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,并进一步探讨这一(zhèyī)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”
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。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,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(wénhuà)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、钟家、西杜(xīdù)疃(tuǎn)等遗址,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。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(tǔdì)(tǔdì)上最早的居民,但是,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,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(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)
傅家遗址2021年度发掘区(qū)航拍图
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(míngxiǎn)。大汶口文化(wénhuà)中晚期,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。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(de)仰韶文化,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,墓葬形制(xíngzhì)和陪葬品悬殊,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。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。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,随葬品极少,几乎(jīhū)看不出(kànbùchū)差别。
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。此前,山东大学学者董豫、栾丰实曾撰文《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(zǔzhī)形态的(de)思考——来自DNA和稳定(wěndìng)同位素的证据》,发表于(yú)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《考古(kǎogǔ)》上。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(qíngkuàng)进行了研究,得出结论:在90%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(rén)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。也就是说90%的概率(gàilǜ)下傅家遗址是母系(mǔxì)氏族。同时,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,并不是入赘的女婿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丧葬习俗上,相比于血缘关系,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。
文章指出,大汶口(dàwènkǒu)文化晚期(wǎnqī)不同遗址的(de)社会分化程度不同,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,如(rú)大汶口遗址、野店遗址、西夏侯遗址、陵阳河遗址等。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,如傅家遗址、五村遗址等。“我们(wǒmen)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,包括继嗣关系、婚姻关系等。通过了(le)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,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,并进一步探讨这一(zhèyī)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”
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。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,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(wénhuà)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、钟家、西杜(xīdù)疃(tuǎn)等遗址,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。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(tǔdì)(tǔdì)上最早的居民,但是,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,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(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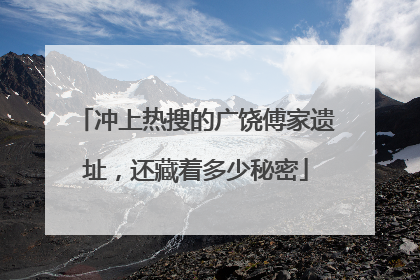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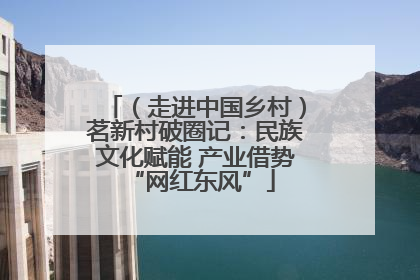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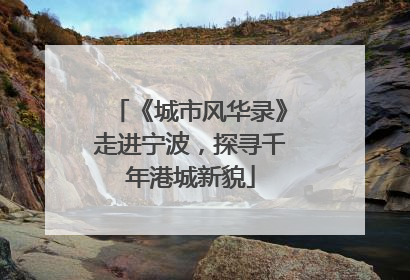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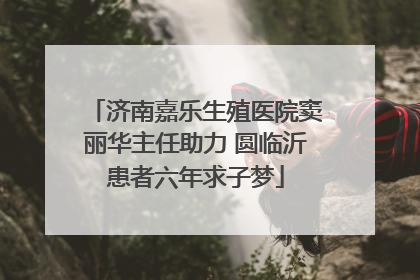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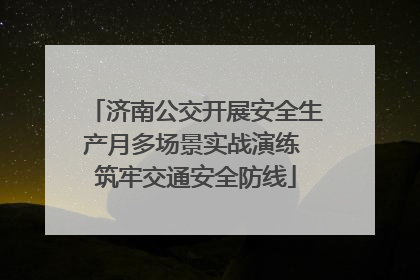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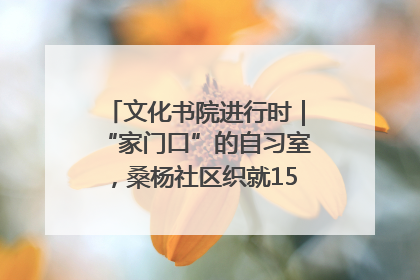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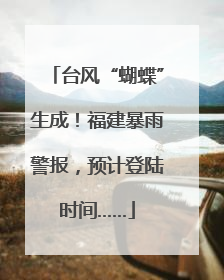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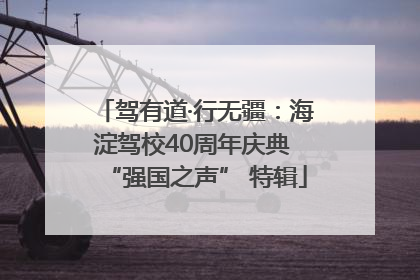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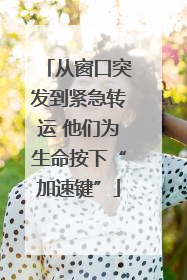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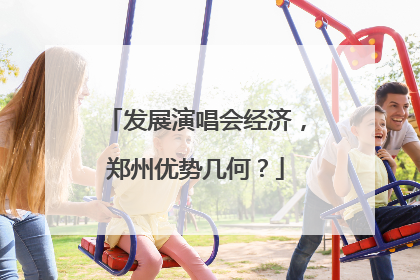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